- 政策解讀
- 經濟發展
- 社會發展
- 減貧救災
- 法治中國
- 天下人物
- 發展報告
- 項目中心
莫理循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關鍵詞: 泰晤士報 袁世凱 朱爾典 丁家立 旁觀者 公共關系 協約國 北京的莫理循 二十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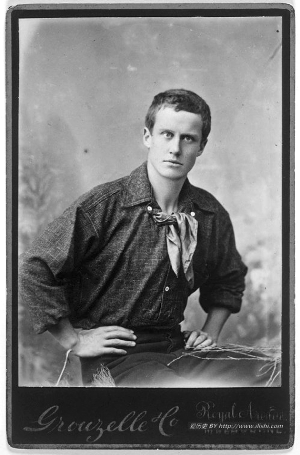
莫理循(1862-1920)
全名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澳大利亞出生的蘇格蘭人,1887年畢業于愛丁堡大學醫科,曾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1897-1912),中華民國總統政治顧問(1912-1920)。1894年,他游歷中國南方,一年后,其游記《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在英國出版。正是因為這本書,他被英國《泰晤士報》賞識,聘為駐中國記者,1897年到北京,開始了他長達17年的記者生涯。
我叫莫理循,澳大利亞人,從事新聞工作。今年是1911年,我在王府井大街100號已經住了9年。正如你們后來看到的那樣,辛亥年是我人生的重大轉折。在北京,我的人脈關系網使我的報道總是領先于其他報紙,新聞界給我很高的評價。中國有句老話,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從旁觀者的角度去看辛亥革命,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隨后的一年,我受聘為中華民國總統政治顧問,也就是袁世凱顧問,我的愛情苦盡甘來,我與珍妮小姐結為夫妻。事業有成,婚姻幸福,人生圓滿,不是嗎?
“旁觀者清”
推袁,只是順水推舟
辛亥革命爆發那天,我去拜訪了赫德的接班人、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以及英國公使朱爾典爵士。據此寫好了新聞稿:“革命爆發和軍隊叛亂的消息已經使北京陷于極度驚慌之中……”電報傳到《泰晤士報》,引起英國輿論的極大關注。
從10月11日至11月24日,我總共發給《泰晤士報》8113個字的電文。在辛亥革命爆發后很長一段時間,由于我的信息來源既有丁家立、青木宣純等美日外交官等等,也有袁世凱的秘書蔡廷干及唐紹儀、梁士詒、汪精衛等人,這些報道的準確性與權威性,是毋庸置疑的。
革命來得太突然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辛亥革命前,我曾寫信給嚴復先生,詢問關于中國政局的問題,嚴復先生用古雅的英文給我回信說,中國應當先搞君主立憲,再過30年搞美利堅合眾國那樣的共和制比較合適。實際上我比較認同嚴復的觀點,對中國政局,我也傾向君主立憲。
但革命爆發沒多久,我就知道我與嚴復先生都錯了。
11月16日,蔡廷干到我家,長談了好幾個小時。他告訴我,君主立憲已經沒有可能,皇室也已意識到處境艱難。
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在北京的革命黨希望我去漢口。英國公使表示贊成,袁世凱也希望我去,并為我準備了專車。這個使命,我很樂意接受,我先到漢口,然后又去了上海和南京。
在上海,我與許多革命黨人見面,指出列強不可能承認孫文或黎元洪,而屬意于袁世凱。我的游說起到了一定效果:革命黨領袖對我說,他們肯定會同意袁世凱為中華民國首任總統。唐紹儀曾經設想,召開國民會議公決政體,這樣可以使袁世凱不用被人指責從孤兒寡婦手中取得天下。
1912年1月5日,我去見袁世凱。袁小聲對我說,再加些壓力,朝廷就垮臺了。1月10日,蔡廷干寫信給我,希望我動員上海商會領頭請愿,要求皇帝退位。我給上海工部局卜祿士寫信提出,請上海商會通過英國公使朱爾典爵士向慶親王和皇帝的父親提出請愿書,說皇室妨礙和平,請皇帝退位。如果上海商會這樣做了,其他商會也會這樣做,聯合起來,力量將會很大。因此,香港、上海的商會都發出了通電。
1月16日,我和羅賓小姐站在王府井大街的寓所門前,等待袁世凱的馬車通過,突然傳來一聲巨大的爆炸聲,幾名革命黨企圖暗殺袁世凱,但失敗了。
不過,很快袁世凱似乎就勝利了。2月12日清帝的退位詔書中講:“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自然,我也率先獨家發表了清帝即將退位的新聞。
作為《泰晤士報》記者,一個中國政局“旁觀者”,對袁世凱的相助,只是錦上添花。我很清楚,這一年,袁世凱縱橫捭闔,謀得總統之位的真正原因,是他在中國毋庸置疑的實力。
“當局者迷”
顧問,“看上去很美”
中國的事情,在1912年年初,似乎看起來已經結束了。皇帝退位,革命黨人得到了共和,袁世凱也做了總統。1912年,對我個人來說,私事是,要正式確定與珍妮·羅賓小姐的關系。另一件事情,可能煩惱得多,是關于中國政府顧問這一角色。
畢竟我已經50歲了,滑膜炎使我的疾病復雜化。出乎意料的是,我招募的秘書珍妮·羅賓,我也越來越被她的女性魅力所傾倒。在1912年4月晴朗宜人的一天,當我和她在寬敞的城墻上散步時,我吐露了對她的愛慕之情。但我比她大27歲,她家里人是否同意?應珍妮的要求,我給她父親寫信求婚。
我曾接到蔡廷干的一封信,請我做中國政府的外國顧問。他在1912年8月2日證實了對我的任命。就在這段時間,我也接到了岳父同意這樁婚事的來信。8月19日,我回到了倫敦,四處游說,接受多家媒體采訪,為袁世凱處理“公共關系”,而且卓有成效。人們都對我的新職表示祝賀,陸軍中將那德·波爾·卡魯爵士等人,讓我幫助找工作。還有很多人,想讓我為他們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許多人要求會面,也讓我應接不暇。在英格蘭南部的南克洛頓,我與珍妮完婚。第二天,我和她在早餐前漫步了14英里,在戶外的池塘邊吃了午飯。
圓滿的婚姻、可觀的薪水、世界性的聲譽,似乎很令人陶醉。但我很快發現,與做《泰晤士報》記者相比,作為中國政府的參謀,我實際上是個擺設,能夠做的事實在有限。北京的政客們,腐敗、墮落,充斥著陰謀與謊言。沒做多少事而享受高薪,并得到袁頒發的“二等嘉禾勛章”,我受之有愧。
在上海時,我曾經對澳大利亞人,《紐約先驅報》記者端納說,你為什么不到革命政府任職?端納說,任何人只要一受雇于中國政府,他的影響就消失了。我當時不以為然,現在我知道,端納是對的。
當時,有關貸款和租界,鴉片和鐵路,西藏和蒙古等問題的爭論無止無休。我為此殫精竭慮,提供了許多咨詢文件。即使建議不被重視,我也照提不誤。宋教仁被暗殺后,國務總理趙秉鈞委任我和伍廷芳對宋案詳盡調查具報。我此前對于中國政府七拼八湊的有關宋案的解釋滿腹狐疑,當即拒絕。
對于我推舉的袁世凱,我看到了他以暗殺、恫嚇和賄賂為政治武器。但是,我做中國政府顧問,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1915年,我與好友端納合作,搶先把袁世凱與日本秘密簽訂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外交密件,披露給《泰晤士報》,將日本的陰謀大白于天下。我還力勸中國加入“協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我這個顧問也算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本文虛擬莫理循自述,參考了竇坤《莫理循與清末民初的中國》、《北京的莫理循》、彼得·湯普森、羅伯特麥克林《中國的莫理循》等著作。